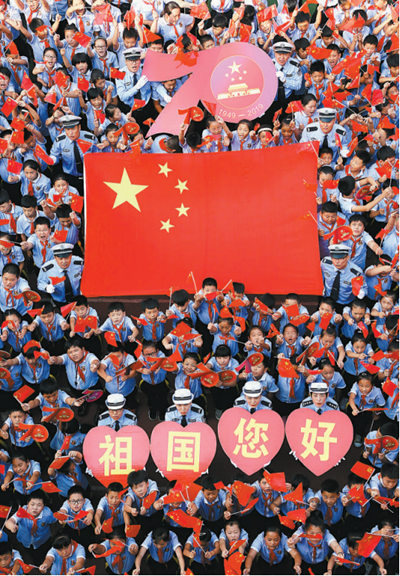
七十年前的那個(gè)秋天,毛澤東莊嚴(yán)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成立,一位詩(shī)人發(fā)出“時(shí)間開始了”的感慨。七十年崢嶸歲月里,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國(guó)慶記憶。這記憶既是個(gè)人成長(zhǎng)的私人敘事,也融入了宏大的家國(guó)歷史,既銘記新中國(guó)創(chuàng)造者和建設(shè)者的豐功偉績(jī),也激蕩著每一個(gè)中國(guó)人熾熱的愛國(guó)情懷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西北之北 我在看不夠的界碑邊升起國(guó)旗
王子冰
16歲那年的冬天,我從寒冷而干燥的豫東平原北上參軍,坐汽車、轉(zhuǎn)火車、乘飛機(jī),用兩天一夜的時(shí)間來(lái)到了新疆阿圖什,成了一名戍守邊疆的戰(zhàn)士。戎馬倥傯十六載,驀然回首,南疆的沙塵、北疆的風(fēng)雪、高原的烈日、邊關(guān)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跡。
邊關(guān),是我人生中最美的風(fēng)景。
10年前的秋天,我到“西北第一哨”白哈巴邊防連任職。那里的冬天雪深天寒,九月十月便開始下雪。當(dāng)時(shí),山里還沒通公路,長(zhǎng)達(dá)半年的“封山期”只能靠自給自足。為了讓戰(zhàn)友們安全順利過冬,我要在國(guó)慶節(jié)前完成所有越冬物資的儲(chǔ)備。直到新中國(guó)60華誕到來(lái),軍地共同組織了一場(chǎng)升國(guó)旗儀式,才讓我暫緩了行程。
白哈巴村生活著哈薩克族、蒙古族、維吾爾族3個(gè)民族,每周一的升旗儀式幾乎雷打不動(dòng)。國(guó)慶當(dāng)天,每個(gè)人更是盛裝出席。我初來(lái)乍到,被那次升國(guó)旗儀式所震撼。
戰(zhàn)士把國(guó)旗拋向天空那一刻,隊(duì)伍里響起了國(guó)歌,不論是蒙古族的耄耋老人,還是哈薩克族的懵懂少年,大家都跟著官兵的節(jié)奏,迎著凜冽的寒風(fēng),唱著心中的民族戰(zhàn)歌。
隊(duì)里有個(gè)名叫加爾恒·坎森的哈薩克族少年,有先天的認(rèn)知障礙,在官兵的幫助下才學(xué)會(huì)識(shí)字、唱歌。他唯一會(huì)唱的歌是《義勇軍進(jìn)行曲》,每次升旗時(shí),都是他最激動(dòng)的時(shí)刻。
后來(lái)我才知道,那時(shí),村里的少數(shù)民族群眾會(huì)說漢語(yǔ)的還不多,官兵在連隊(duì)開辦了“漢語(yǔ)教學(xué)班”,報(bào)名的人很多,最想學(xué)的就是國(guó)歌。
關(guān)山萬(wàn)重,祖國(guó)在每個(gè)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模樣。在這個(gè)西北邊陲的小牧村里,她同樣偉大而神圣。
不久后,白哈巴迎來(lái)了入冬后最大的一場(chǎng)雪。一夜之間,孤零零的哨所便如同漂在雪海中的一葉小舟,封山期開始了。封山期最怕停水、停電。連隊(duì)飲用的是雪水,用電主要靠配發(fā)的柴油發(fā)電機(jī)。遇到地下管道凍住或發(fā)電機(jī)損壞,生活就變得格外艱難。
但是,只要有機(jī)會(huì),我依然會(huì)騎著駿馬,背著鋼槍,穿行在邊關(guān)的風(fēng)雪里,去瞻仰國(guó)境線上的一座座界碑。
在旁人眼里,界碑或許只是一磚一石,但在我們心里,重逾千斤。
封山期的時(shí)光很慢,日子就像界河里凍住的水,似乎靜止了一般。我每天都會(huì)站在二樓俱樂部的窗戶前,隔著玻璃,遙望遠(yuǎn)處的雪山。直到來(lái)年四五月份,山上的雪像被扯脫線的白毛衣,一點(diǎn)點(diǎn)褪到山頂,露出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青松時(shí),春天就來(lái)了。
界碑旁有一片松樹林,俯瞰其輪廓頗像祖國(guó)的版圖,官兵便稱其為“中華林”。為了讓“中華林”名副其實(shí),一茬茬官兵不斷地修剪、移植、補(bǔ)種,每年國(guó)慶節(jié),大家巡邏到這里,都會(huì)站在“中華林”前,進(jìn)行一次宣誓,用鏗鏘的誓言吼出滿腔的忠誠(chéng)。
“西北之北,大雪紛飛。走不完的巡邏路,看不夠的界碑……”后來(lái),我寫了一首關(guān)于邊防的歌,這首《西北之北》在朋友圈里連續(xù)幾天被“刷屏”。
祖國(guó)的邊關(guān)越來(lái)越美。白哈巴修通了公路,接入了市電,網(wǎng)絡(luò)也覆蓋到周邊的牧區(qū),以后不會(huì)再有“封山期”。資訊發(fā)達(dá)的時(shí)代,牧民借助旅游開發(fā)富了起來(lái),也忙了起來(lái)。但每周一的升旗儀式從未間斷,每家每戶的門楣上都插上了國(guó)旗,清風(fēng)徐來(lái),像一片紅色的海洋。
今年國(guó)慶節(jié)是新中國(guó)70華誕,除了升國(guó)旗儀式,白哈巴還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一臺(tái)主題晚會(huì)。除了維吾爾族的“麥西來(lái)甫”、哈薩克族的“黑走馬”、蒙古族的頂碗舞,我和戰(zhàn)友還為晚會(huì)創(chuàng)作了歌曲《為祖國(guó)站崗》,只等那天軍民同臺(tái),普天同慶。
我每次休假回家,總被朋友問起:“邊關(guān)那么苦,為啥你總說邊關(guān)很美?”“當(dāng)兵那么久,真的不會(huì)膩嗎?”其實(shí),我很想告訴他們,邊關(guān)最美的不是風(fēng)景,而是守衛(wèi)在那里的那群人。他們從懵懂無(wú)知到眼明心亮,從當(dāng)兵吃餉到心懷家國(guó),所追逐的不是一人之利,而是一國(guó)之安。
阿爾泰山物產(chǎn)豐富,每座哨所都處在邊境前沿,許多盜獵、盜采的人員總會(huì)利用各種手段躲過盤查、遁入深山或越過邊境,我聽許多老兵講起過他們與盜山者之間的斗智斗勇。狼群報(bào)恩、哈熊襲營(yíng)、山盜謎蹤之類的故事,總讓我聽得欲罷不能。鐵打的營(yíng)盤流水的兵,我希望這些故事能夠流傳下去,讓后來(lái)的戰(zhàn)友續(xù)寫這些故事時(shí),也傳承起這種精神。
守衛(wèi)一條邊防線,刻下一生戍邊情。桌上的日歷越來(lái)越薄,預(yù)示著我的軍旅時(shí)光所剩無(wú)幾。我知道,今后無(wú)論走到哪里,邊關(guān)已和我的生命融為一體,衛(wèi)國(guó)戍邊的情懷永遠(yuǎn)都不會(huì)變。
(感謝“一號(hào)哨位”對(duì)本文約稿的支持)
無(wú)數(shù)難忘日夜只為那個(gè)偉大時(shí)刻
陶西平
1949年10月1日清晨,我和同學(xué)們一道,排著整齊的隊(duì)伍,迎著晨曦,滿懷豪情地走向天安門,參加開國(guó)大典。為了迎接這個(gè)偉大的日子,我們經(jīng)歷了無(wú)數(shù)個(gè)難忘的日夜。
我在1948年考入北平四中,也就是新中國(guó)成立后的北京四中。那時(shí)國(guó)民黨政權(quán)已經(jīng)奄奄一息,無(wú)人顧及教育,學(xué)校破爛不堪。由于通貨膨脹,要用一袋面粉繳納學(xué)費(fèi)。初中年級(jí)已經(jīng)沒有完整的課桌椅,學(xué)生要抽簽自備桌椅。我家從東單小市買了一套舊課桌椅,我的同桌李敖從家里搬來(lái)一張小八仙桌。還有同學(xué)摞起幾塊磚頭,上面放一塊木板當(dāng)課桌。
開學(xué)3個(gè)多月后,我們到學(xué)校才發(fā)現(xiàn),國(guó)民黨士兵在校門口站崗,不許進(jìn)校,連書包都不許取出來(lái)。原來(lái),傅作義的部隊(duì)已經(jīng)把學(xué)校作為陣地,操場(chǎng)上架起4門大炮,軍隊(duì)駐扎在校園里,連我們的課桌椅也被當(dāng)成柴火燒了。
學(xué)校停課到年底,忽然有的同學(xué)傳來(lái)消息,希望大家回校。我們回校時(shí),看到校長(zhǎng)室前的地面上整齊地放著一排排步槍。國(guó)民黨兵躲在屋子里,不出來(lái)了。當(dāng)我正在納悶時(shí),幾位高中同學(xué),后來(lái)知道他們是地下黨的同志,站在椅子上,對(duì)大家激情滿懷地說:北平已經(jīng)和平解放,傅作義軍隊(duì)就要出城整編,解放軍就要進(jìn)城了,希望同學(xué)們一起歡迎解放軍進(jìn)城。同學(xué)們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(lái)。
接著,我和不少同學(xué)一道,每天來(lái)到學(xué)校,學(xué)唱革命歌曲《東方紅》《你是燈塔》《解放區(qū)的天》,用彩色的紙做小旗子,聽解放區(qū)的故事。1949年年初,北京四中的隊(duì)伍在西四牌樓的路邊,揮舞著小旗,高唱著歌曲,歡迎從西直門進(jìn)城的解放軍坦克和戰(zhàn)車上豪邁的戰(zhàn)士。
不久,地下黨和老區(qū)來(lái)的同志接管了學(xué)校,學(xué)校開始復(fù)課。那時(shí),黨在青年中的外圍組織還沒有公開。但是,在學(xué)校里建立了進(jìn)步的圖書社,在圖書社里除了有毛主席等領(lǐng)導(dǎo)同志的著作,還有趙樹理等作家的小說,像《李家莊變遷》《李有才板話》等。不少同學(xué)去看書,實(shí)際是接受革命的啟蒙教育。1949年4月,新民主主義青年團(tuán)成立,5月地下黨的青年外圍組織成員公開身份并轉(zhuǎn)為團(tuán)員,原來(lái)我所在的班里已有兩位中國(guó)民主青年聯(lián)盟的成員,他們也是我最早相識(shí)的團(tuán)員。
當(dāng)時(shí),最令人激動(dòng)的是在平津解放以后,大軍南下,捷報(bào)頻傳的時(shí)刻。4月南京解放,5月西安、上海解放。每有喜訊傳來(lái),同學(xué)們就上街游行慶祝,白天舉著紅旗,晚上提著燈籠,一路高歌,一路歡呼。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南下工作團(tuán),開辟新解放區(qū)的工作,于是學(xué)校里又掀起參加南工團(tuán)的熱潮,四中許多高年級(jí)同學(xué)甚至還有初中同學(xué)踴躍報(bào)名,隨軍南下。
當(dāng)年7月,北京市為了加強(qiáng)學(xué)校的革命隊(duì)伍建設(shè),成立了大中學(xué)生暑期學(xué)習(xí)團(tuán)。在黨員班主任和班上團(tuán)員的影響下,我已申請(qǐng)入團(tuán),所以也被允許進(jìn)入學(xué)習(xí)團(tuán)學(xué)習(xí),這是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礎(chǔ)的重要時(shí)刻。學(xué)習(xí)團(tuán)的主任是彭真同志,有4個(gè)分團(tuán),三分團(tuán)主要是中學(xué)生,分團(tuán)主任是汪家镠同志。我們每天早晨提著馬扎,唱著歌排著隊(duì)去會(huì)場(chǎng)聽報(bào)告,聽了艾思奇、胡繩、劉瀾濤、榮高棠等領(lǐng)導(dǎo)和專家的報(bào)告,學(xué)習(xí)了社會(huì)發(fā)展史、黨史、學(xué)生運(yùn)動(dòng)等理論。
在8月燦爛的星空下,我和一批同學(xué)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北京大學(xué)民主廣場(chǎng)上莊嚴(yán)宣誓,成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(tuán)團(tuán)員。
接著,就是迎接中國(guó)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(huì)議召開和開國(guó)大典。當(dāng)時(shí),天安門廣場(chǎng)還是丁字形,堆積著多年未清理的垃圾,同學(xué)們和許多群眾一道來(lái)到廣場(chǎng)進(jìn)行清理,在垃圾的底層甚至還發(fā)現(xiàn)明清時(shí)代的殘留。大家揮汗如雨,但心情舒暢,每個(gè)人都希望讓廣場(chǎng)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(guó)的啟航。
1949年10月1日上午,北京四中同學(xué)穿著當(dāng)時(shí)最美的禮服——白衫、藍(lán)褲子,早早地來(lái)到天安門廣場(chǎng),雖然位置離城樓較遠(yuǎn),但個(gè)個(gè)精神抖擻。大家席地而坐,高唱革命歌曲,等待那莊嚴(yán)的時(shí)刻到來(lái)。下午3點(diǎn),廣播喇叭里傳來(lái)毛主席洪亮的聲音,宣布“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”,頓時(shí)廣場(chǎng)紅旗飄舞,萬(wàn)眾歡騰。接著舉行閱兵式,我們仰頭看著飛機(jī)轟鳴著飛過蔚藍(lán)的天空,感到無(wú)比自豪。閱兵式后,我們起身開始游行,校旗飄舞在隊(duì)伍的前面,從廣場(chǎng)游行到學(xué)校,已是夜晚,但大家心潮澎湃,仍然歡呼歌唱,還扭起了剛剛學(xué)會(huì)的秧歌,久久不肯散去。
70年前的這一天,鐫刻在中國(guó)的歷史上;迎接這一天的日日夜夜,鐫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,也深深地鐫刻在我們的心里。
(作者系國(guó)家教育咨詢委員會(huì)委員、聯(lián)合國(guó)教科文組織協(xié)會(huì)世界聯(lián)合會(huì)榮譽(yù)主席)
曾經(jīng)的中國(guó)驕傲至今讓人念念不忘
薛一博
離開中國(guó)多年的阿塞拜疆著名漢學(xué)家、前總統(tǒng)戰(zhàn)略研究中心亞洲國(guó)家內(nèi)外政策首席顧問拉沙德·卡里莫夫先生,對(duì)10年前在中國(guó)工作時(shí)的一段經(jīng)歷仍念念不忘。2009年,拉沙德是阿塞拜疆共和國(guó)駐華大使館的一名外交人員,親歷了國(guó)慶60周年慶典。
回憶當(dāng)時(shí)親歷的場(chǎng)景,拉沙德描述得清晰而具體。歡樂的人群、飄揚(yáng)的紅旗、大紅的燈籠、藍(lán)天白云下的天安門和華表,都給他帶來(lái)醒目而強(qiáng)烈的視覺沖擊。尤其是,“20萬(wàn)軍民參與的盛大閱兵儀式,讓我除了感到雄偉、壯觀、驚嘆、震撼,還有感動(dòng)”。
在中國(guó)學(xué)習(xí)、生活、工作多年,精通漢語(yǔ)的拉沙德先生當(dāng)然了解中國(guó)的發(fā)展?fàn)顩r和成就,他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中國(guó)社交網(wǎng)絡(luò)上也看到了網(wǎng)民們自然流露出的濃濃自豪感。“神舟飛船”“國(guó)產(chǎn)大飛機(jī)”“高峽出平湖”“高原天路”“磁懸浮列車”“北京奧運(yùn)會(huì)”“一國(guó)兩制”……這些詞語(yǔ)一個(gè)個(gè)從他的口中蹦出。拉沙德還引用了他從網(wǎng)絡(luò)上看到的一個(gè)說法兒,新中國(guó)60年,早就從“油燈歲月”發(fā)展到了“網(wǎng)絡(luò)時(shí)代”。
拉沙德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散發(fā)出濃厚的“中國(guó)氣息”,如果只聞其聲不抬頭看人,你會(huì)誤以為是在跟一個(gè)純正的中國(guó)人對(duì)話。拉沙德說:“你可以叫我的中文名字,羅仕德。我與中國(guó)很有緣分,我曾經(jīng)在這個(gè)國(guó)家學(xué)習(xí)、生活、工作了15年。是中國(guó)培養(yǎng)了我,毫不夸張地說——如果沒有在中國(guó)這些年的經(jīng)歷,就沒有現(xiàn)在的我。”
拉沙德·卡里莫夫是土生土長(zhǎng)的阿塞拜疆人。1995年,他以優(yōu)異成績(jī)考入巴庫(kù)國(guó)立大學(xué)中文系,并在一年后通過一項(xiàng)教育合作協(xié)議赴北京語(yǔ)言大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,自此與中國(guó)結(jié)緣。在北語(yǔ)本科畢業(yè)后,拉沙德留在中國(guó)深造,先后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(xué)位。然后,他選擇留在中國(guó)工作,參與阿塞拜疆駐華使館的工作,為外交事業(yè)作貢獻(xiàn)。
在北京的求學(xué)和工作經(jīng)歷,是拉沙德“最為懷念的時(shí)光”;親歷新中國(guó)成立60周年慶典活動(dòng),則是他在中國(guó)15年的“精彩瞬間”之一。直到現(xiàn)在,每次去北京出差,他總會(huì)回到母校坐一坐,見見老師和同學(xué)。2017年,由他編撰的《漢語(yǔ)阿塞拜疆語(yǔ)詞典》由中國(guó)商務(wù)印書館出版,這本工具書實(shí)現(xiàn)了拉沙德早就萌發(fā)的一個(gè)理想,盡管“編寫詞典的過程非常耗費(fèi)精力。但看到了越來(lái)越多的阿塞拜疆青少年在學(xué)習(xí)漢語(yǔ),這讓我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(fèi),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
新中國(guó)即將迎來(lái)成立70周年的日子,拉沙德接著前面談到的“油燈時(shí)代”“網(wǎng)絡(luò)時(shí)代”話題說,僅僅10年過去,用“網(wǎng)絡(luò)時(shí)代”已經(jīng)遠(yuǎn)遠(yuǎn)不能描述現(xiàn)在的中國(guó)。即便是用現(xiàn)在流行的“5G時(shí)代”“人工智能時(shí)代”等,也不足以描述中國(guó)的發(fā)展?fàn)顩r。“新中國(guó)即將慶祝成立70周年,雖然今年我不能親歷今年的隆重慶祝活動(dòng),但10年前的經(jīng)歷,讓我能夠想象即將在中國(guó)、在北京出現(xiàn)的盛況。中國(guó)是一個(gè)偉大的國(guó)家,它有著更加光明的未來(lái)。”





